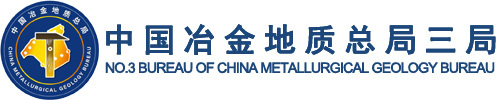路灯下的小老头
发布时间:
2022-11-10
作者:
刘 喆
来源:
岩土公司
访问量:
分享至:
夏日黄昏的天空,多情的落日留下一抹橘红,与悬挂的月牙儿争辉,路灯发出了惺忪的光亮。
马路上的人多了起来,那种解脱一天禁锢奔向自由的热情,掀起了城市里喧嚣的浪。漫步其中,见证着城市日新月异的美好。路边驻足的人很多,散散步、遛遛狗,听听孩子们嬉戏打闹之声、商贩吆喝叫卖之声……是这样的充满奔放的活力。
领着孩子,顺着马路,向着汾河公园走去。路边有个老头儿,架起一台老式爆米花机,开始经营他的生活。或许,他觉得只有在这里,爆米花出锅时像闷炮一样的炸响声,才不会惊扰到别人吧。
不一会儿,他便把爆出的大米花、玉米花用袋装好,整整齐齐地摆在了前面。这是个没有人围观的地方,尽管这个古老的设备,偶尔能唤起大人们对童年的回忆,吸引小孩子好奇的目光,但在这个地方驻足的少之又少。人们越来越讲究卫生饮食,很少有人会买这个东西。
每当有人在他的小摊前多瞅两眼或减速通过,都会被他敏锐地捕捉到,那说不清是脏还是熏黑亦或就是肤色暗沉的脸上,立刻堆起笑容,从地上一骨碌站起来,殷勤道:“来一包吧,三块钱,没有添加的。”这一脸笑容可以持续到客人走得只剩背影,他便讪讪地又坐回原地。
天越来越黑,我路过他,继续向前走去,不时回过头看看,却始终不知道他偶尔发愣时眼睛看向何方。
过了天桥,到公园里,各种舞曲的声音、踢毽子的呐喊声、清脆悦耳的乐器声,彰显着人们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。
溜达了一大圈,我原路返回了。远远地,又看到了他。他已经把所有的“家伙事”收拾停当,放在了脚踏三轮车上。一把扫帚在他手中卖力地工作着。这个地方,除环卫工人,很少有人在用过后把它收拾干净。他不过是临时占用一下,没有弄得很脏,况且天这么黑了,谁也不会在意,他却扫得一丝不苟。
走了好久,忽然想起,我对他的衣着居然没有分毫印象,只依稀记得,那斑驳的树荫漏了些许路灯的光斑在他身上,但他佝偻着的背和堆砌的笑却清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不觉得他是个“有文化”的人,可偏偏想起了著名文学家梁晓声对“文化”二字的解读:植根于内心的修养,无需提醒的自觉,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,为别人着想的善良。
在这个人心浮躁的社会,路灯下的小老头儿,应该算是个文化人吧。